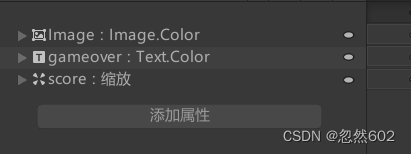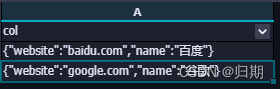暗夜直至黎明
坐在冰冷的地板上,咬噬着手中的梨,本应是炎热的夏季,莫名的雨却下的很快乐。
不喜欢梨的味道,只是因为它有很多汁水,会顺着指间滴落,在漆黑的夜里,无声寂寞地下坠。
就是这样面无表情地盯着自己晃动的影子。梨已经残缺不全,喉头依然干涸,犹如心上的某一块地方,水过无痕。
说不上是不是有自虐的倾向,喜欢,正确地说,应该是习惯长久地吃一样食物,一直吃到自己反胃,想吐为止。从此,便不再碰它。有心理书说,这是喜新厌旧的一种另类表现。是吗?可是在享受食物带来的美味时,我是愉悦的;抛弃它时,又没有一丝丝的后悔,这又该如何解释呢?
书上所指的多半是风花雪月的事。生活是道大餐,爱情充其量只能是饭后甜品。顶多留下暂时的余香,却永远不可能填饱肚子。人们钟爱它的理由,无非是诱人的外表。而看到的、幻想中的和吃进嘴中的截然是两码不同的事。
空调工作的嗡嗡声,搅动着平和。整间屋子好象幻化成了一滩水。而我,是一条鱼。一条不会游泳的鱼。仿佛又置身于小时候的那一场灾难。浮动在海中,望见的只有身上滑动的水和模糊的天空。现在想起来,那时的海是愿意接受自己的。没有令人心悸的窒息,一切都很自然。随后,突然,一阵猛力将自己拽出海面。新鲜的空气全压进肺里。剧烈的咳嗽。自己并没有意识到危机的过去,只是全身的血液,一下子安静下来,心里充满疼痛。过了这么久,仍然忘不了那种被撕裂的感觉。
对于疼痛,早已麻木,头部、手、五脏、腿。身体的每一部分。都经历过,余下的屈指可数。也不曾惧怕惨不忍睹,急诊室里的血肉模糊。在别人的哭叫喊叫,只是就默默站立一边,脸上没有任何惶然。
无数次感到来自内心深出的呼喊,什么东西蠢蠢欲动,象要蓄势待发,找寻着解脱。于是,每到深夜,执着刀片沿着白皙的手腕就这么轻轻地按下去。缓缓流淌地是重获自由的鲜红。抱着缠着纱布的手,在仍旧残留血腥气息的夜风中安然入睡。
曾有人说,你是个让人不安的人。我摇摇头,我从不面对面的看过一个人。这个答非所问使对方一脸的困惑。人真的是一种奇怪的动物。同样的话,知己清楚,朋友糊涂,陌生人则全然不明所以。俞伯牙和钟子期的友谊境界,是自己的追求。但五年、十年,亲眼目睹着自己从希望走到失望,最后过渡到了绝望。网上一个朋友指责我,你可以放弃梦想,但你没有权利漠视它。对着这行字,我独自笑了很久,他是对的。而我,只是不知道绝望背后是否还有路继续可走。
雨悄无声息地停了。天开始发白。躺在木板上,隔着落地窗地布幔,盯着乌蓝的天空,一点一点地亮起来。凌晨的寒意不知不觉地登堂入室。
不知曾几何时,爱上了风过耳的感觉。尤其是强风,那种凄厉的声音,象是某一种动物的呜咽。贯穿耳膜,直达灵魂。很多人坐过海盗船。当船身脱离地心引力飞速运动,一股强大的气流似要把人四分五裂。极少的人玩过蹦极,一跃而下的快意,风在每个呼吸通道乱窜,到底的释放。旅行的时候有过“会当凌绝顶”的机会,展开双臂立在兀出的岩石上,身下便是万丈深渊,林海无顷。半个小时过去了,终究丧失跳下去的勇气。山鹰在头顶盘旋,我俯下身子,告诉自己只是因为缺少一对翅膀,并非惧怕死亡。可泪却无声无息地掉落下来,满脸的湿意。
朦胧中,有电话在响。自己竟然睡着了。等到艰难握住话筒时,对方挂断了。生活每天都在重复无聊的游戏。用冷水泼泼脸,镜中的人有着淡淡的眼圈。梳理头发后,水池里又多了几簇显眼的黑色。自己无奈地牵牵唇角。
拉开布幔,橘色的阳光兜头而来。弹触皮肤后,落在地上裂成了一地碎片。生命清醒着,可还有什么东西,它依旧在沉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