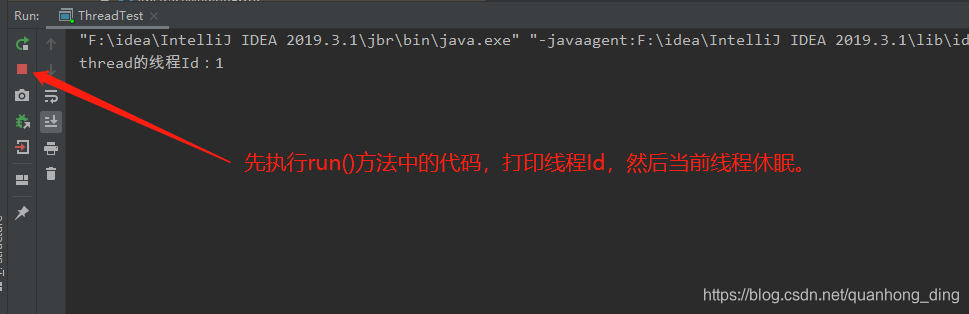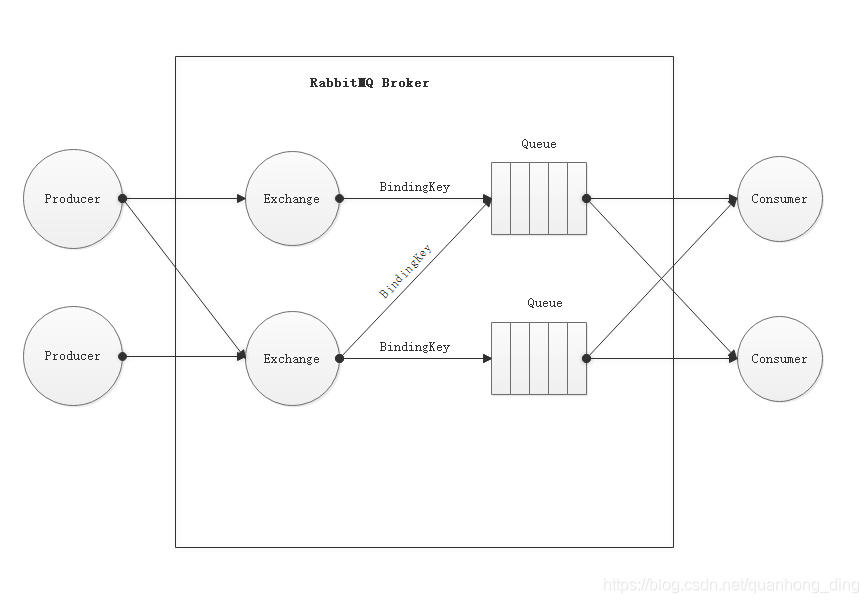像西方知识分子那样登场
文/鸿帆 
大陆这些年被批判得最凶的几位“知识分子”,都是在大众媒体上表现活跃的“明星学者”。余秋雨的作品被贬为“文化口红”,易中天被指责“胡说三国”,刘 心武被国内红学家集体炮轰……于丹只是那一串被批判名单中的一个新名字。人们不禁要问:这些明星学者为何总是处于“风暴中心”?是因为他们确实很“差”, 还是因为其他的文人嫉妒他们所取得的声名?
在笔者以为,与其在这上面浪费时间,不如换一个角度来思考问题。眼下更为要紧的事情是,我们应该让 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走上大众媒介的平台。因为,只有让更多优秀的知识分子,积极地、智慧地、主动地介入大众传媒,公众的视野中才会不断有一流的人物出现, 当那些真正的大师现身,担当起这个时代的教化工作,向大众供应思想的愉悦与旷达的时候,那些二流、三流的角色,自然会被淘汰到被人们遗忘的角落。
西方知识分子批判大众媒体,秉持学术追求
在西方,很多一流的知识分子都在电视上长篇大论,中国的同行们在这方面比他们晚了将近半个世纪。某个大学教授就某段新闻发表评论,或者两位专家就某项政 策争得面红耳赤,早已成为西方电视荧屏上常见的风景。值得一提的是,那些专家学者在镜头前一个个都能说会道、表情丰富,其风采丝毫不亚于专业主持人。
西方的知识分子之所以积极参与大众媒介,与西方人对于“知识分子”这个词的理解息息相关。写下《知识分子论》的著名学者爱德华·W·萨义德认为,知识分 子便是具有能力向公众以及代公众表达讯息、观点、态度、哲学或意见的个人。而在古德纳看来,知识分子就该走向台前,向民众发出自己的声音。弗兰克·富里迪 也直截了当地指出,成为知识分子便意味着社会参与。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很难既为思想而活,又不试图去影响社会,那这就意味着他们不仅参与到创造性的思想活 动中,而且也必须担负起社会责任。
西方知识分子对于以电视为代表的大众媒介的态度颇为复杂。一方面,他们对大众媒体基本持批判态度,知道媒体 和学术的追求方向——前者以收视率为标准,后者则有其自身的学术规范——存在着根本的差异;另一方面,他们又知道,身为一名现代知识分子,没有理由放弃媒 介。庞德、萨特、波伏娃、约翰·伯格、以赛亚·伯林等现代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均深度涉入媒体。
萨特失明后,放弃写作,全力主持面向法国和全 欧洲的电视节目长达10年之久;约翰·伯格在BBC主持多年系列节目,几乎影响到1970年代后的欧美文化形态;美国的重要学者、文人甚至总统都不介意接 受《花花公子》的采访,甚至很高兴自己的访谈出现在丰乳肥臀的照片之间,因为那意味着自己有关中东问题、哲学问题或福利问题的看法可以触及到广大的人群。 在英国,用电视来“布道”的知识分子,其耀眼程度,可以把人气旺盛的真人秀和肥皂剧比下去。
笔者在英国留学的时候就认识了一些教授,他们无一例外都乐意在电视上、报纸上发表自己的见解。其中,有一位名叫戴维·迪肯(David Deacon)的学者,每每在介绍自己学术成就时都会骄傲地提到,他每个星期都在《卫报》上发表一篇评论。
通过其他手段接近大众
这些年,欧洲的社会学界出现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几位社会学大师(比如英国的吉登斯、褒曼、法国的鲍德里亚)写出的著作越来越薄、越来越浅,有时还会给书起上一个诱人的书名(比如褒曼的新著《流动的爱》),很显然,那是为了吸引非学术人士。
有些知识分子甚至是写畅销书的高手,比如刚刚来华访问过的意大利学者安贝托·艾柯。艾柯在学术界的专业是符号学,不过让他的名字广为人知的是他的小说。 他的《玫瑰之名》让人在追踪一个险象环生的连环杀人案的同时了解到与《圣经》、中世纪和亚里士多德相关的知识;《傅科摆》在故事中套入了数学、物理学、神 学、史学、政治学乃至历法学,而新作《波多里诺》涉及十字军东征、圣杯传说、基督教城市的兴起、教皇与皇帝之间的权力冲突、修道院阴谋、阿基米德的镜子、 传说中的东方祭司王国等等文化概念——如果想了解这些知识,那么你很难找到比艾柯的书更精彩、更好看的入门教材。
大陆知识分子应承担责任
眼下,正是中国知识分子积极融入传媒时代的时候。
一个可供知识分子振臂高呼的舞台已经搭好。从报纸、杂志,到电视、电台,直至新兴的网络传媒,中国如今拥有的是一个完善而庞大的传媒体系。相关部门对于 媒介内容的监管依然存在,但是尺度比起过去松了很多。更为重要的是,媒介在今日中国的力量正变得前所未有的强大。于丹为什么火?一个重要的原因,不是因为 她拥有教授、博士、系主任等诸多头衔,更不是因为她“四岁就学《论语》”,而是因为她有机会在“黄金周”的时候走进央视百家讲坛,陈述“心得”。
而另一方面,舞台下的观众也已经做好准备、嗷嗷待哺。在这个科技迅速发展、生活瞬息万变、人文花果凋敝的时代,人们渴望获取知识、获得信息、感悟精神、拥有思想。易中天也好,于丹也罢,他们的如日中天,恰恰说明了普罗大众对于文化知识和精神食粮的渴望。
值得一提的是,今天的大部分电视观众,都已具备了一定的文化素质,他们对于文化产品有渴求,也有辨识。正因如此,他们能从争鸣的百家中,分辨出真正智慧的声音,人道的声音,高尚的声音。这对于一流的知识分子来说,显然是个福音。
在这样的时候,中国的知识分子应该承担起人文精神构建和倡导的职责,整体性地走出书斋,走向大众,身体力行,言传身教。
掌握走向传媒的技巧
不过,话说回来,将媒介作为一项工具的运用,并不像想象的那么简单。要利用传媒,知识分子仅凭一腔热血和满腹经纶是不够的;大众媒介的特点决定了,他们必须要掌握一定的技巧。
比如说,要想在电视上受人欢迎,那么掌握一些面对镜头的技巧是十分必要的。据说,一旦面对镜头,易中天就更像一个经验老到的明星,而非久居象牙塔的博 导;他知道什么姿势坐得最不舒服,上镜拍出来就最好看。而许多和易中天学识相当的学者,在镜头前就表现不出那分从容,让电视导演不得不忍痛割爱。
余秋雨也谈到过类似的问题:“十几年来,我坚持与电视文化结合,一直走到今天,突然发现,以前那些不断反对我上电视的文人,现在也偶尔在电视上露脸了,只不过他们觉醒太晚,出场匆忙,表情和衣着总是不太妥当。”
而如果学者们决定不上电视、只通过书本和大众交流,那不妨学学艾柯,试着写写寓教于乐的畅销书;学不了艾柯还可以学褒曼,把学术文章写得平易近人。毕 竟,学术不一定要远离大众,不一定要用刻板方式和抽象表述才可能达其真意,不一定要坚守正统理念的威严而不与个体权利发生联系。
当然,这些都只是技巧,知识分子在修习这些技巧的时候,不要忘了自己在传媒中的真正优势,那就是知识、智慧与公共良心。
文/鸿帆
http://blog.sina.com.cn/u/4b8bd145010008e4
一方面,一个可供知识分子振臂高呼的传媒舞台已经搭好;另一方面,知识饥渴、精神饥渴的观众也已就座。现在,就剩下请大陆知识分子——
一方面,一个可供知识分子振臂高呼的传媒舞台已经搭好;另一方面,知识饥渴、精神饥渴的观众也已就座。现在,就剩下请大陆知识分子——
大陆这些年被批判得最凶的几位“知识分子”,都是在大众媒体上表现活跃的“明星学者”。余秋雨的作品被贬为“文化口红”,易中天被指责“胡说三国”,刘 心武被国内红学家集体炮轰……于丹只是那一串被批判名单中的一个新名字。人们不禁要问:这些明星学者为何总是处于“风暴中心”?是因为他们确实很“差”, 还是因为其他的文人嫉妒他们所取得的声名?
在笔者以为,与其在这上面浪费时间,不如换一个角度来思考问题。眼下更为要紧的事情是,我们应该让 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走上大众媒介的平台。因为,只有让更多优秀的知识分子,积极地、智慧地、主动地介入大众传媒,公众的视野中才会不断有一流的人物出现, 当那些真正的大师现身,担当起这个时代的教化工作,向大众供应思想的愉悦与旷达的时候,那些二流、三流的角色,自然会被淘汰到被人们遗忘的角落。
西方知识分子批判大众媒体,秉持学术追求
在西方,很多一流的知识分子都在电视上长篇大论,中国的同行们在这方面比他们晚了将近半个世纪。某个大学教授就某段新闻发表评论,或者两位专家就某项政 策争得面红耳赤,早已成为西方电视荧屏上常见的风景。值得一提的是,那些专家学者在镜头前一个个都能说会道、表情丰富,其风采丝毫不亚于专业主持人。
西方的知识分子之所以积极参与大众媒介,与西方人对于“知识分子”这个词的理解息息相关。写下《知识分子论》的著名学者爱德华·W·萨义德认为,知识分 子便是具有能力向公众以及代公众表达讯息、观点、态度、哲学或意见的个人。而在古德纳看来,知识分子就该走向台前,向民众发出自己的声音。弗兰克·富里迪 也直截了当地指出,成为知识分子便意味着社会参与。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很难既为思想而活,又不试图去影响社会,那这就意味着他们不仅参与到创造性的思想活 动中,而且也必须担负起社会责任。
西方知识分子对于以电视为代表的大众媒介的态度颇为复杂。一方面,他们对大众媒体基本持批判态度,知道媒体 和学术的追求方向——前者以收视率为标准,后者则有其自身的学术规范——存在着根本的差异;另一方面,他们又知道,身为一名现代知识分子,没有理由放弃媒 介。庞德、萨特、波伏娃、约翰·伯格、以赛亚·伯林等现代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均深度涉入媒体。
萨特失明后,放弃写作,全力主持面向法国和全 欧洲的电视节目长达10年之久;约翰·伯格在BBC主持多年系列节目,几乎影响到1970年代后的欧美文化形态;美国的重要学者、文人甚至总统都不介意接 受《花花公子》的采访,甚至很高兴自己的访谈出现在丰乳肥臀的照片之间,因为那意味着自己有关中东问题、哲学问题或福利问题的看法可以触及到广大的人群。 在英国,用电视来“布道”的知识分子,其耀眼程度,可以把人气旺盛的真人秀和肥皂剧比下去。
笔者在英国留学的时候就认识了一些教授,他们无一例外都乐意在电视上、报纸上发表自己的见解。其中,有一位名叫戴维·迪肯(David Deacon)的学者,每每在介绍自己学术成就时都会骄傲地提到,他每个星期都在《卫报》上发表一篇评论。
通过其他手段接近大众
这些年,欧洲的社会学界出现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几位社会学大师(比如英国的吉登斯、褒曼、法国的鲍德里亚)写出的著作越来越薄、越来越浅,有时还会给书起上一个诱人的书名(比如褒曼的新著《流动的爱》),很显然,那是为了吸引非学术人士。
有些知识分子甚至是写畅销书的高手,比如刚刚来华访问过的意大利学者安贝托·艾柯。艾柯在学术界的专业是符号学,不过让他的名字广为人知的是他的小说。 他的《玫瑰之名》让人在追踪一个险象环生的连环杀人案的同时了解到与《圣经》、中世纪和亚里士多德相关的知识;《傅科摆》在故事中套入了数学、物理学、神 学、史学、政治学乃至历法学,而新作《波多里诺》涉及十字军东征、圣杯传说、基督教城市的兴起、教皇与皇帝之间的权力冲突、修道院阴谋、阿基米德的镜子、 传说中的东方祭司王国等等文化概念——如果想了解这些知识,那么你很难找到比艾柯的书更精彩、更好看的入门教材。
大陆知识分子应承担责任
眼下,正是中国知识分子积极融入传媒时代的时候。
一个可供知识分子振臂高呼的舞台已经搭好。从报纸、杂志,到电视、电台,直至新兴的网络传媒,中国如今拥有的是一个完善而庞大的传媒体系。相关部门对于 媒介内容的监管依然存在,但是尺度比起过去松了很多。更为重要的是,媒介在今日中国的力量正变得前所未有的强大。于丹为什么火?一个重要的原因,不是因为 她拥有教授、博士、系主任等诸多头衔,更不是因为她“四岁就学《论语》”,而是因为她有机会在“黄金周”的时候走进央视百家讲坛,陈述“心得”。
而另一方面,舞台下的观众也已经做好准备、嗷嗷待哺。在这个科技迅速发展、生活瞬息万变、人文花果凋敝的时代,人们渴望获取知识、获得信息、感悟精神、拥有思想。易中天也好,于丹也罢,他们的如日中天,恰恰说明了普罗大众对于文化知识和精神食粮的渴望。
值得一提的是,今天的大部分电视观众,都已具备了一定的文化素质,他们对于文化产品有渴求,也有辨识。正因如此,他们能从争鸣的百家中,分辨出真正智慧的声音,人道的声音,高尚的声音。这对于一流的知识分子来说,显然是个福音。
在这样的时候,中国的知识分子应该承担起人文精神构建和倡导的职责,整体性地走出书斋,走向大众,身体力行,言传身教。
掌握走向传媒的技巧
不过,话说回来,将媒介作为一项工具的运用,并不像想象的那么简单。要利用传媒,知识分子仅凭一腔热血和满腹经纶是不够的;大众媒介的特点决定了,他们必须要掌握一定的技巧。
比如说,要想在电视上受人欢迎,那么掌握一些面对镜头的技巧是十分必要的。据说,一旦面对镜头,易中天就更像一个经验老到的明星,而非久居象牙塔的博 导;他知道什么姿势坐得最不舒服,上镜拍出来就最好看。而许多和易中天学识相当的学者,在镜头前就表现不出那分从容,让电视导演不得不忍痛割爱。
余秋雨也谈到过类似的问题:“十几年来,我坚持与电视文化结合,一直走到今天,突然发现,以前那些不断反对我上电视的文人,现在也偶尔在电视上露脸了,只不过他们觉醒太晚,出场匆忙,表情和衣着总是不太妥当。”
而如果学者们决定不上电视、只通过书本和大众交流,那不妨学学艾柯,试着写写寓教于乐的畅销书;学不了艾柯还可以学褒曼,把学术文章写得平易近人。毕 竟,学术不一定要远离大众,不一定要用刻板方式和抽象表述才可能达其真意,不一定要坚守正统理念的威严而不与个体权利发生联系。
当然,这些都只是技巧,知识分子在修习这些技巧的时候,不要忘了自己在传媒中的真正优势,那就是知识、智慧与公共良心。
来源:《凤凰周刊》2007年第9期总第25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