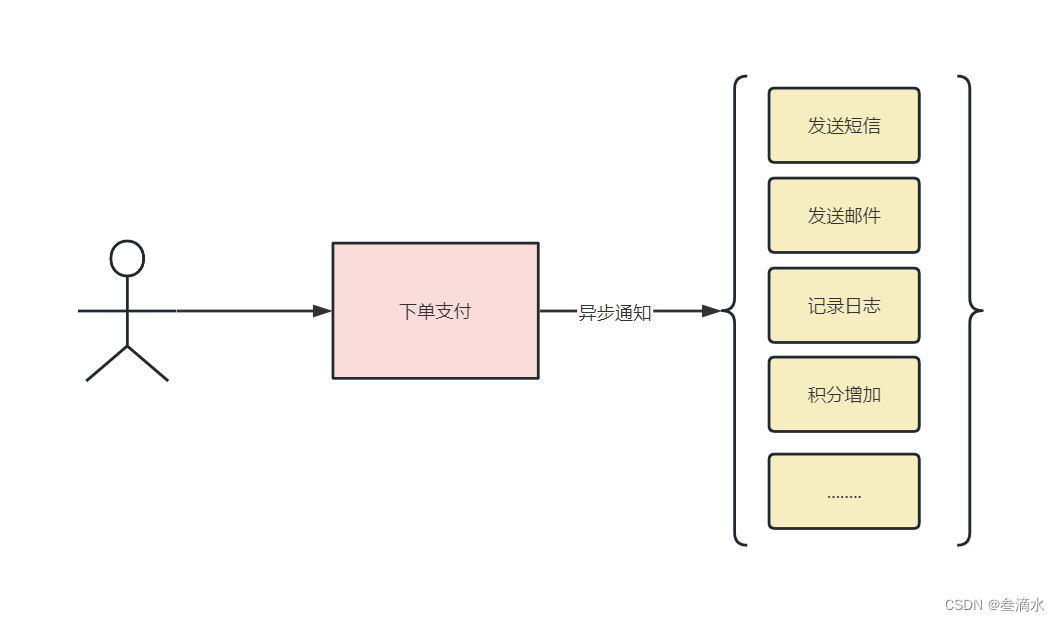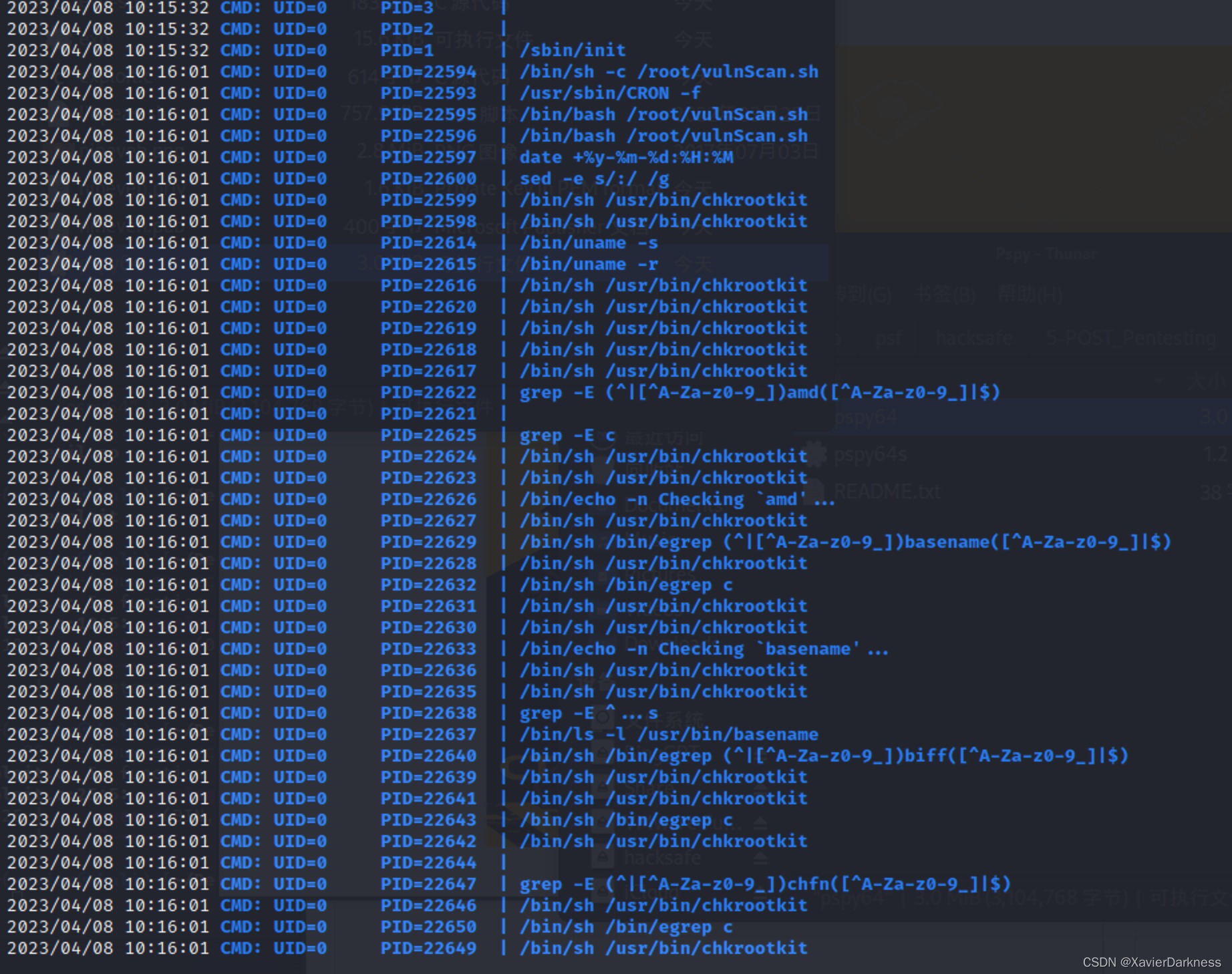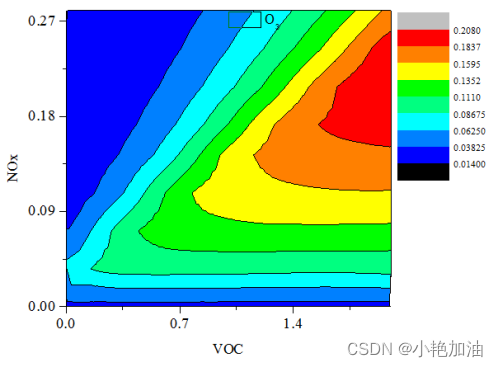目录
感悟
经典摘录
假若我再上一次大学
不完满才是人生
走运与倒霉
毁誉
我的座右铭
二月兰
观天池
火车上观日出
感悟
- 人这个万物之灵却偏偏有了感情,有了感情就有了悲欢。
- 自古及今,海内海外,一个百分之百完满的人生是没有的,这种说法适用于一切人,旧社会的皇帝老爷子也包括在里面
- 走运与倒霉
- 毁誉:我主张对毁誉要加以细致的分析。首先要分清:谁毁你?谁誉你?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由于什么原因?这些情况弄不清楚,只谈毁誉,至少是有点模糊。
经典摘录
假若我再上一次大学
- “假若我再上一次大学”,多少年来我曾反复思考过这个问题。我曾一度得到两个截然相反的答案:一个是最好不要再上大学,“知识越多越反动”,我实在心有余悸。一个是仍然要上,而且偏偏还要学现在学的这一套。后一个想法最终占了上风,一直到现在。
- 我为什么还要上大学而又偏偏要学现在这一套呢?没有什么堂皇的理由。我只不过觉得,我走过的这一条道路,对己,对人,都还有点好处而已
- 我的大学生活是比较长的:在中国念了四年,在德国哥廷根大学又念了五年,才获得学位。我在上面所说的“这一套”就是在国外学到的。我在国内时,对“这一套”就有兴趣。但苦无机会。到了哥廷根大学,终于找到了机会,我简直如鱼得水,到现在已经坚持学习了将近六十年。
- 如果想让我谈一谈在上大学期间我收获最大的是什么,那是并不困难的。在德国学习期间有两件事情是我毕生难忘的,这两件事都与我的博士论文有关联。我想有必要在这里先谈一谈德国的与博士论文有关的制度。当我在德国学习的时候,德国并没有规定学习的年限。只要你有钱,你可以无限期地学习下去。德国有一个词儿是别的国家没有的,这就是“永恒的大学生”。德国大学没有空洞的“毕业”这个概念,只有博士论文写成,口试通过,拿到博士学位,这才算是毕了业。
- 教授认为你“孺子可教”,才会给你一个博士论文题目。再经过几年的努力,收集资料,写出论文提纲,经过教授过目。论文写成的年限没有规定,至少也要三四年,长则漫无限制。拿到题目十年八年写不出论文,也不是稀见的事。所有这一切都决定于教授,院长、校长无权过问。写论文,他们强调一个“新”字,没有新见解,就不必写文章。见解不论大小,唯新是图。论文题目不怕小,就怕不新。我个人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只有这样,学术才能“日日新”,才能有进步。
- 我拿到博士论文题目的过程,基本上也是这样。我拿到了一个有关佛教混合梵语的题目。用了三年的时间,搜集资料,写成卡片,又到处搜寻有关图书,翻阅书籍和杂志,大约看了总有一百多种书刊。然后整理资料,使之条理化、系统化,写出提纲,最后写成文章。
- 于是我想在论文一开始就写上一篇“导言”,这既能炫学,又能表现文采。真是一举两得的绝妙主意,我照此办理。... 然而却使我大吃一惊。教授在我的“导言”前面画上了一个前括号,在最后画上了一个后括号,笑着对我说:“这篇导言统统不要!你这里面全是华而不实的空话,一点新东西也没有!别人要攻击你,到处都是暴露点,一点防御也没有!”对我来说,这真如晴天霹雳,打得我一时说不上话来。
- 第二件事情是,论文完成以后,口试接着通过,学位拿到了手。论文需要从头到尾认真核对,不但要核对从卡片上抄入论文的篇、章、字、句,而且要核对所有引用过的书籍、报纸和杂志。
要知道,在三年以内,我从大学图书馆,甚至从柏林的普鲁士图书馆,借过大量书籍和报刊,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当时就感到十分烦腻。现在再在短期内,把这样多的书籍重新借上一遍,心里要多腻味就多腻味。
- 德国书中的错误之少,是举世闻名的。有的极为复杂的书竟能一个错误都没有,连标点符号都包括在里面。读过校样的人都知道,能做到这一步,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德国人为什么能做到呢?他们并非都是超人的天才,他们比别人高出一头的诀窍就在于他们的“笨”。我想改几句中国古书上的话:“德国人其智可及也,其笨(愚)不可及也。”
- 反观我们中国的学术界,情况则颇有不同。在这里有几种情况。中国学者博闻强记,世所艳称。背诵的本领更令人吃惊。过去有人能背诵四书五经,据说还能倒背。写文章时,用不着去查书,顺手写出,即成文章。但是记忆力会时不时出点问题的。
中国近代一些大学者的著作,若加以细致核对,也往往有引书出错的情况。这是出上乘的错。等而下之,作者往往图省事,抄别人的文章时,也不去核对,于是写出的文章经不起核对。这是责任心不强,学术良心不够的表现。还有更坏的就是胡抄一气。
只要书籍文章能够印出,哪管他什么读者!名利到手,一切不顾。我国的书评工作又远远跟不上。即使发现了问题,也往往“为贤者讳”怕得罪人,一声不吭
不完满才是人生
- 然而,自古及今,海内海外,一个百分之百完满的人生是没有的。所以我说,不完满才是人生。关于这一点,古今的民间谚语、文人诗句,说到的很多很多。最常见的比如苏东坡的词:“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南宋方岳(根据吴小如先生考证)的诗句:“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
- 这种说法适用于一切人,旧社会的皇帝老爷子也包括在里面。他们君临天下,“率土之滨,莫非王土”,可以为所欲为;杀人灭族,小事一端。按理说,他们不应该有什么不如意的事。然而实际上,王位继承、宫廷斗争,比民间残酷万倍。他们威仪俨然地坐在宝座上,如坐针毡。虽然捏造了“龙驭上宾”这种神话,但他们自己也并不相信。他们想方设法以求得长生不老。。。
- 在这些皇帝手下的大臣们,“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权力极大,骄纵恣肆;贪赃枉法,无所不至。在这一类人中,好东西大概极少,否则包公和海瑞等绝不会流芳千古,久垂宇宙了。可这些人到了皇帝跟前,只是一个奴才,常言道:伴君如伴虎,可见他们的日子并不好过。
- 现在我们运气好,得生于新社会中。然而那一个“考”字,宛如如来佛的手掌,你别想逃脱得了。幼儿园升小学,考;小学升初中,考;初中升高中,考;高中升大学,考;大学毕业想当硕士,考;硕士想当博士,考。考,考,考,变成烤,烤,烤;一直到知命之年,厄运仍然难免。现代知识分子落到这一张密而不漏的天网中,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我们的人生还谈什么完满呢?
走运与倒霉
- 走运与倒霉,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绝对对立的两个概念。世人无不想走运,而决不想倒霉。
其实,这两件事是有密切联系的,互相依存的,互为因果的。说极端了,简直是一而二二而一者也。这并不是我的发明创造。两千多年前的老子已经发现了,他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其无正。”老子的“福”就是走运,他的“祸”就是倒霉。
-
吾辈小民,过着平平常常的日子,天天忙着吃、喝、拉、撒、睡,操持着柴、米、油、盐、酱、醋、茶。有时候难免走点小运,有的是主动争取来的,有的是时来运转,好运从天上掉下来的。高兴之余,不过喝上二两二锅头,飘飘然一阵了事。但有时又难免倒点小霉,“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没有人去争取倒霉的。倒霉以后,也不过心里郁闷几天,对老婆、孩子发点小脾气,转瞬就过去了。
-
但是,历史上和眼前的那些大人物和大款们,他们一身系天下安危,或者系一个地区、一个行当的安危。他们得意时,比如打了一个大胜仗,或者倒卖房地产、炒股票,发了一笔大财,意气风发,踌躇满志,自以为天上地下,唯我独尊。“固一世之雄也”,怎二两二锅头了得!然而一旦失败,不是自刎乌江,就是从摩天高楼跳下,“而今安在哉”!
-
从历史上到现在,中国知识分子有一个“特色”,这在西方国家是找不到的。中国历代的诗人、文学家,不倒霉则走不了运。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司马迁算的这个总账,后来并没有改变。汉以后所有的文学大家,都是在倒霉之后,才写出了震古烁今的杰作。像韩愈、苏轼、李清照、李后主等一批人,莫不皆然。几乎从来没有过状元宰相成为大文学家的。
-
了解了这一番道理之后,有什么意义呢?我认为,意义是重大的。它能够让我们头脑清醒,理解祸福的辩证关系:走运时,要想到倒霉,不要得意过了头;倒霉时,要想到走运,不必垂头丧气。心态始终保持平衡,情绪始终保持稳定,此亦长寿之道也。
毁誉
- 好誉而恶毁,人之常情,无可非议。
古代豁达之人倡导把毁誉置之度外。我则另持异说,我主张把毁誉置之度内。置之度外,可能表示一个人心胸开阔;但是,我有点担心,这有可能表示一个人的糊涂或颟顸。
我主张对毁誉要加以细致的分析。首先要分清:谁毁你?谁誉你?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由于什么原因?这些情况弄不清楚,只谈毁誉,至少是有点模糊。
- 我们常常讲什么“党同伐异”,又讲什么“臭味相投”等等。这样的毁誉能相信吗?
- 孔门贤人子路“闻过则喜”,古今传为美谈。我根本做不到,而且也不想做到,因为我要分析:是谁说的?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点,因为什么而说的?分析完了以后,再定“则喜”,或是“则怒”。喜,我不会过头。怒,我也不会火冒十丈,怒发冲冠。孔子说:“野哉,由也!”大概子路是一个粗线条的人物,心里没有像我上面说的那些弯弯绕。
- 我自己有一个颇为不寻常的经验。我根本不知道世界上有某一位学者,过去对于他的存在,我一点都不知道;然而,他却同我结了怨。因为,我现在所占有的位置,他认为本来是应该属于他的,是我这个“鸠”把他这个“鹊”的“巢”给占据了。因此,勃然对我心怀不满。我被蒙在鼓里,很久很久,最后才有人透了点风给我。我知道,天下竟有这种事,只能一笑置之。不这样又能怎样呢?我想向他道歉,挖空心思,也找不出丝毫理由。
- 由于各人禀赋不同,遗传基因不同,生活环境不同,所以各人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好恶观等等,都不会一样,都会有点差别。比如吃饭,有人爱吃辣,有人爱吃咸,有人爱吃酸,如此等等。又比如穿衣,有人爱红,有人爱绿,有人爱黑,如此等等。在这种情况下,最好是各人自是其是,而不必非人之非。俗语说:“各扫自家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这话本来有点贬义,我们可以正用。每个人都会有友,也会有“非友”,我不用“敌”这个词儿,避免误会。... 最好抱上面所说的分析的态度,切不要笼而统之,一锅糊涂粥。
好多年来,我曾有过一个“良好”的愿望:我对每个人都好,也希望每个人对我都好。只望有誉,不能有毁。最近我恍然大悟,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如果真有一个人,人人都说他好,这个人很可能是一个极端圆滑的人,圆滑到琉璃球又能长上脚的程度。
我的座右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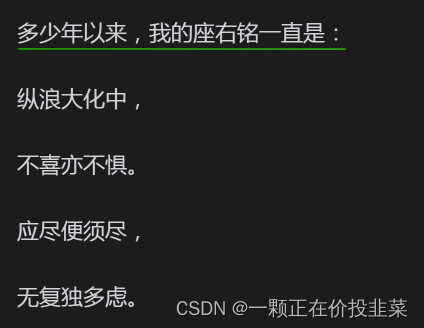
老老实实的、朴朴素素的四句陶诗[插图],几乎用不着任何解释。
- 到了现在,自己已经九十多岁了。离人生的尽头,不会太远了。我在这时候,根据座右铭的精神,处之泰然,随遇而安。我认为,这是唯一正确的态度。
- 所谓老年忧郁症恐怕十有八九同我上面提出的看法有关,怎样治疗这种病症呢?我本来想用“无可奉告”来答复。但是,这未免太简慢,于是改写一首打油诗,题曰“无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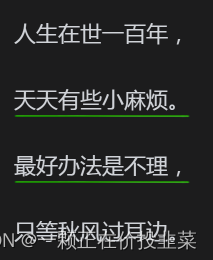
二月兰
- 我不记得从什么时候起注意到小山上的二月兰。这种野花开花大概也有大年小年之别的。碰到小年,只在小山前后稀疏地开上那么几片。遇到大年,则山前山后开成大片。二月兰仿佛发了狂。我们常讲什么什么花“怒放”,这个“怒”字用得真是无比地奇妙。二月兰一“怒”,仿佛从土地深处吸来一股原始力量,一定要把花开遍大千世界,紫气直冲云霄,连宇宙都仿佛变成紫色的了。东坡的词说:“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此事古难全。”但是花们好像是没有什么悲欢离合。应该开时,它们就开;该消失时,它们就消失。它们是“纵浪大化中”,一切顺其自然,自己无所谓什么悲与喜。我的二月兰就是这个样子。
- 二月兰是不会变的,世事沧桑,于她如浮云。然而我却是在变的,月月变,年年变。我想以不变应万变,然而办不到。
- 我当时日子实在非常难过。我知道正义是在自己手中,可是是非颠倒,人妖难分,我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答,一腔义愤,满腹委屈,毫无生人之趣。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成了“不可接触者”,几年没接到过一封信,很少有人敢同我打个招呼。我虽处人世,实为异类。
- 我还有一件心事:我想弄清楚,什么叫“悲”?什么又叫“欢”?是我成为“不可接触者”时悲呢?还是成为“极可接触者”时欢?如果没有老祖和婉如的逝世,这问题本来是一清二白的。现在却是悲欢难以分辨了。我想得到答复。
观天池
- 尖劲的山风,千万年来,把它们已经制得服服帖帖,趴在地上,勉强苟延残喘,口中好像是自称“奴才”,拜倒在山风脚下连呼“万岁”了。
- 我一下子就想到了盛名传播四海的天池水怪。在平静的碧波下面,他们此时在干些什么呢?是在操持家务呢?还是在开会?是在制造伪劣商品呢?还是在倒买倒卖?是在打高尔夫球呢?还是在收听奥运会的广播?是在品尝粤菜的生猛海鲜呢?还是在吃我们昨天在延吉吃的生鱼片?……问题一个个像连成串的珍珠,剪不断,理还乱。
- “你看这人类多么可笑!在普天之下,五湖四海,争名夺利,勾心斗角,胜利了或者失败了,想出来散散心,不远千里,不远万里,冒着生命危险,来到我们这里
火车上观日出
- 走到了列车的走廊上。猛一抬头,我的全身连我的内心立刻激烈地震动了一下:东方正有一抹胭脂似的像月牙儿一般的红彤彤的东西腾涌出来。这是即将升起的朝阳,我心里想。
- 我在泰山和黄山这两个在全中国甚至全世界都以能观日出而声名远扬的名山上,看到了日出。是我自己处心积虑一意追求而得来的。
我现在是在火车上,既非泰山,也非黄山。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会同观赏日出联系起来,我一点寻求的意思也没有。然而,仿佛眼前出现了奇迹:摆在我眼前的是不折不扣的日出。我内心的震惊不是完全很自然的吗?
- 它让我暂时离开了尘世,离开了火车,甚至离开了我自己。我体会到变中有不变,不变中又有变;我体会到变化与速度的交互融合,交互影响。